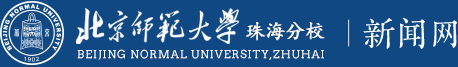1900年,因维新变法失败而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先生,在他的历史名文“少年中国说”中充满痛楚地疾呼:“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如今,已经整整一个世纪多过去了,我们要问,少年中国梦实现了吗?
中华民族曾经有过“少年中国”的时代。中国好几位对人类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孔子,老子,孙子 …全都出在那个时代,然而,自从秦始皇实现了大一统,特别是在他开了“焚书坑儒”的先例之后,“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之风,中国就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唯有在20世纪之交,中央政权失去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曾有过短暂的对西方各种新思潮的开放)。从此以后,虽然我们对人类文明贡献了“四大发明”的技术,却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能够影响世界的思想家。这究竟是为什么?有人以为,这是因为从此以后,宽松的学术环境,以及知识分子被捧为座上宾的地位,再也没有出现过了。从此以后权力高于一切,而学术只能沦为它的奴裨,知识分子再也不允许有自己的独立人格,科举制度还进一步让知识分子以借助四书五经来帮助统治阶级建立思想统治,来换取分享权力的特权。从此以后,中国的权威文化顺应了封建政治体制的需要,开始牢固建立起来,异端邪说再也不被允许,青年人只能捧读先贤的经典,不能越雷池一步。百姓们只能以吏为师,官员不仅管征税,而且统管老百姓脑子里的东西。统治阶级的权力和作为“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度,培育了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扼杀了创造力,培育了一味顺从的性格。”(L. S. Stavrianos A GLABAL HISTORY)对祖先权威的崇拜,使中国无法勇敢地吸收先进的文化,眼看着原本是自己学生的东邻后来居上。少年的中国从此蜕变成老人的中国,官僚的中国。哀哉,中国。伤哉,中国。
一场又一场改革的失败,一次又一次流血的教训,莫不提醒我们,现代化的科学,现代化的政治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其实都产生在现代文化的土壤中,中国如果没有文化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塑造出中国人的少年人格,就不可能建立现代化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充分实现人的价值,就不可能有一流的大学,一流的科学,不可能有完全的现代化,使人民过上高度幸福的生活。
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的进步必然伴随着个人价值的充分实现。然而,在中国要建立现代化的高度尊重个性的文化,能够单靠对传统文化的挖掘来完成吗?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也有一些很有人性的思想,例如孔子的一整套“仁”的思想,这些思想曾经对文艺复兴发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可 能奢求两千多年以前的孔子,要求他也能高度尊重人的个性。事实上,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在农耕社会的氏族群体结构中,它也是扼杀个性的文化,儒家学说的一个核心是“礼”,即尊卑有序的等级结构。这种礼教文化要求个人无条件服从等级结构的群体价值观。而“礼”恰恰是历代统治者竭力加以推广,因此形成全社会行为规范的思想。鲁迅先生所痛斥的“吃人”的文化就是这种礼教文化。正是这种礼教文化(权威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扼杀了中国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维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要想利用孔子的“仁”去打倒他的“礼”,无异于让一个人用左手去打倒他的右手。这么做客观上起到的作用,也许恰恰是用他的“仁”去维护他的“礼”。中国历代的独裁者,哪一个不善于使用这一套手段呢?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古希腊文化的辉煌建立在地中海各种文化交流的基础上,文艺复兴吸收了古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营养。同时冲破了“圣人”亚力斯多德的框架,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人人享有各种政治上,思想文化上的权利的崭新观念。从而产生出支撑现代化国家的民主文化的土壤。中国要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同样必须敢于批判权威,敞开胸怀,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
然而,尽管我们吸收先进文化的过程才缓慢地行进了30年左右的时间,有人就跳出来说,五四运动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错了。有人又在大叫要让孩子从小读经。似乎又在试图重建孔家店。我们要问,“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错了吗?孔家店其实是指中国权威文化的殿堂,是尊卑有序的殿堂,礼教的殿堂。企图打倒孔家店的先驱者,如陈独秀,蔡元培,梁启超等人,莫不是饱读诗书,熟愔传统文化的大儒,他们要打倒的是礼教的殿堂,然而他们都继承了“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传统价值观。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果不能搬开礼教的绊脚石,会有各种新思想,包括马列主义的传播吗?会有婚姻自由吗?会有中国人现在能够享有的一些起码的自由吗?
我们更加要问的是:五四运动所呼唤的德先生真的已经来到中国人民中间了吗?他已经成为我们的国民性的组成部分了吗?问一问那些在中国文化与民主文化中都生活过多年的人,他们一般都会坚决地摇头。文化最终会表现为人的行为规范,在中国人的行为规范中,渗透了太多权威文化的痕迹。 那么究竟为何德先生依然没有成为中国国民性的一个主要成分呢?
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民族矛盾占据了统治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呐喊很快就被救亡的呼声所淹没。民族情结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和潜意识层面占据了突出的位置。想要以传统文化作为基本文化格局的保守派们,往往乘机打出了民族主义的旗帜,对一些文化的冲突冠以“反华” 的标签,企图阻碍先进文化进入中国的步伐。使我们中国人迟迟不能焕发青春的光彩,使我们在外来文化前面不能像日本那样,成为一个虚心好学的少年,而总是崇拜权威,依附群体。这种权威文化的历史包袱,何其沉重,它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又一个的历史机遇,产生一个又一个的民族悲剧。而全体中国人一起高呼万岁,一起去蹂躏人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悲剧的登峰造极。如今,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30多年了,尽管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已经迈出了不少步子,但是其步履依然蹒跚,火烧圆明园的烈焰仍然在电视上和中国人的心目中不停地回放。民族的情结依然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敏感的伤痛点。很多人一听说某些外国人跟我们有点儿过不去,也不去仔细地研究其原因,就以为他们在“反华”,马上就投入了“抵制”的群体。看来,如何更好地面对外来文化,这一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面临的最大历史课题,今天仍然存在。
为了让我们能够代表先进的文化,为了让我们真正实现少年的,而不是老人的文化,我们首先要在文化的桥头堡—大学中培育这种文化,让她孕育出少年中国人。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校园里的情况吧。
文化的壁垒首先是语言造成的,其实以英语作为大学的教学语言,早就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因为英语已经成为现代科学和文化的主要载体。英语是我们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和其他各种先进文化习俗的主要工具。不能熟练地掌握这一基本工具,我们无法站在世界的前列。中国不少学科的科研水平低,某些学科甚至仍然走着国外半个多世纪前走过的老路,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英语水平低,不了解这一领域的新动态。
从多伦多大学留学回来的大学钱伟长早就提出,大学生最重要的基础是英语。而中国的学生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大学毕业时仍然只会考试,不会听说读写,主要原因就在于语言学习与专业学习和日常应用脱节。
在珠海分校有不少学生,大部分时间用来谈恋爱,上网,也照样能混到毕业证。有些内地来的学生进校后看到校风如此淫糜,痛心疾首,大叫上当,宁可退学。双语课教学能使懒汉学生进入角色。使他们养成少年人应有的勤奋的习惯,使我校的学风建设走上正轨。为国家培养出合格的人才。
推行双语教育,也是通过教学相长,提升教师科研实力,同时整顿教风的基本途径。在珠海分校,某些50岁以下的中年教师在提高级职称时,都不需要考外语,他们写的书尽管其涉及的是国内最为薄弱的领域,却没有用到一项外文资料。这无形中在培养弄虚作假的作风。目前国内盛行浮躁文化,如果大学教师都在搞浮躁风,那就无疑是中国人的悲哀。我们太需要真诚的少年文化!
既然双语教学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师生,为什么我们总是难以启动双语教学的车轮呢,完全是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吗?
有一位在国外留学过多年的教师,他对双语的需要,有着太痛切的体会。曾多次与领导沟通,希望尽快推行双语教学,然而都没有得到支持,领导告诉他,这是有比例控制的,他提出要申报,领导说,不是由你来申报,而是由我们来安排。这位教师知道,尽管这位领导是非常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对于双语却完全是外行。而且他想的更多的也许是上级的意图,而不是学生们迫切的需要。所以这位教师太能够理解,为什么华生校长一上台就能够大张旗鼓地推行双语教学,因为华生校长与钱伟长校长一样,不是行政官员,而是学者,他们能够深刻地理解学生的需要。
有些“长辈”之所以反对双语,除了利益冲突外,也似乎有着民族的情节在推动他们,他们似乎觉得上双语就丢失了“国格”,一听说要用英语教学,马上就加以反对,而不少领导当然是听这些“权威”的。但是“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梁启超语),为将来计,我们必须尽快采用英语教学,因为英语已经成为全球化的语言。
双语教学是一项刻不容缓的系统工程,必须下大力气尽快地推动起来,否则对不起学生,对不起家长。通过这一工程,有助于培育出面向世界的,勤奋踏实的少年人和少年文化。
实行双语教学,需要勤考试,因此我们需要尽快实行机器改卷,国外在十多年前就实现了这一步。有一位教授曾多次向领导提过这方面的建议,但是在他(她)所在的单位,教授的意见很少被采纳过。
在实行双语教学的同时,我们要更加重视中文(大学语文)的教学,学生的语文水平,特别是他们的写作水平,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我们的优势是双语,而不是单纯的英文。在提高学生思想文化素质的过程中,中英文是可以相互帮助的,然而基础仍然是中文。没有丰富思想的人是缺乏创造力的,而语言是思想的载体。
为了培育充满活力的,充分尊重个性,尊重知识的文化,我们首先必须对教授高度的尊重,高度的信任。真正实现教授治校,而不是官员治校。以教授为中心,而不是以官员为中心,就会形成学术的中心,而不是权力的中心。有一位在国外留学多年的教授告诉笔者说,他在一所世界第一流的名牌大学工作了多年,几乎没有看到过院长或系主任,每次活动都是教授主持,有些教授的办公室比院长、主任的都大。凡是与专业有关的问题,都是该领域的专家说了算,权限非常的分明。他在国外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我信任你”。在这样的氛围中,人的积极性就被充分调动起来了。中国古代早就有这么一句话,“士为知己者用之”。然而在珠海分校某些单位,某些官员(他们确实是一些处处想负起责任的好官员)对于教授的专业建议,也会用权力来顶回去,例如,某教授建议为受培训的教师提供一本他著译的教材,有一位掌实权的官员就觉得教授是为了突出自己,马上用软的办法顶了回去。有些官员甚至认为他们单位的教授素质不高,因而不能搞教授治校。属下的素质如何,自然是由官员来评定的,中国历来如此。
少年的文化不是论资排辈的文化,而是确实相信“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文化,确实相信“自古英雄出少年”的文化。但是在珠海分校的某些部门,却总是觉得老教授就是万能的专家,尽管任何教授从事的总是一个特殊的领域,但是在这些部门,任何学术问题都让一两个老教授去作决断,。尽管老教授都很有高风亮节,但是在无意识中,他们不知不觉地仍然扮演着“老师”的角色。这种老人文化,在强调“百年老校”的北师大,似乎还颇有一点市场。记得多年以前著名学者张志超曾写过一篇名为“中国学术界的结构性变动”的文章,指出文革前毕业的知识分子,由于受到政治的冲击太大,外语水平也不高,因而其学术水平实际上受到了很大的局限。但是老人文化却仍然刻意地拔高他们。这种风气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年轻教师看到老教授,待之以长辈之礼,奉茶敬烟。而老教授则以和蔼,亲切的目光注视着晚辈。老教授一言既出,青年人噤若寒蝉,无人敢去挑战。我们在民主的文化中看到的却是:宽容,鼓励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年轻人的“出格”看法。在那里虽然有学术的专家,却不存在辈分。因此不断有新思想,新学派的产生。而我们这里,年轻的学子们似乎生来就特别相信教授的牌子。而不问其真才实学。这类权威文化的痕迹,到处可以见到。在中国,一言堂虽然从理论上早就被否定,群言堂在生活中却只能让位于“辈分堂”和“权力堂”。谁之过也?年轻人?老年人?老百姓?官员?
少年的文化是创新的文化,求异的文化。“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创新能力首先体现在我们的文风之中。然而,60多年前毛泽东所痛斥的“党八股”,如今仍然阴魂不散。学生讲话连用语都是照搬照抄的,极少有自己的新鲜语言。而教授有个性,似乎成了一种错误。这种作风当然不是珠海分校的特产,当时,我们为什么不能开风气之先呢?在民主的文化中,我们看到,他们处处强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鼓励个性。教师的讲话往往生动风趣,充满个性的。个性是多样性和创造性的源泉,我们生活在一个创新时代,一个知识时代。知识产权和品牌构成了产品的主要价值。个性也是民主的基础。只有当每一个人都展现出自己的少年风采,我们才会有一个真正少年的中国,创新的中国。
少年文化当然并非专属于年龄上的少年人,“世有老少年,亦有少年老,”少年文化属于真正的少年中国人。
啊!珠海分校,我们期待着您,无愧于孙中山,梁启超的故乡,无愧于这一片无比秀美的南粤山川,我们期待着您,在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培育出充满生机的少年文化,民主文化,养育出千千万万的少年骄子,千千万万充满个性的创造者,他们将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挑战传统文化的糟粕,他们将敞开胸怀,尽情地吸收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同时,他们也将善于继承中华文化的精华。他们会在强调个性的同时,在个体与群体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
啊!少年中国,我梦中的美女,你比貂蝉更娇艳,因为你不再依附任何“英雄”,也不再摧眉折腰于任何权贵。你不仅善于展现自己独特的才艺,更敢于亮出自己思想的锋芒。你比西施更妩媚,因为你不仅更为自信,而且更加健壮,充满生命的活力。你鄙夷一味模仿、剽窃的东施式行为,对于那些敢于以独特的风采来挑战你,超越你的少年才子,却情有独钟。你展现出大自然的健康美,推陈出新的创造美,而摒弃了数千年不变的凝固的美。你开怀的笑,你雍容坦荡的风采,自然也比蒙娜丽莎更为迷人,因为你有海纳百川的博大。在你的心胸之中,各种异域的情调,各种不同的声音,无论是正调还是反调,都是你能够吸收营养的源泉。你心中回响着的是具有中华特色的人类优秀文化的交响乐。而它的主题则是人类共同的:“人”。啊,少年中国,有多少怀着一颗少年心的中国人思念着您。少年中国,我似乎已经看到,你正在款款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