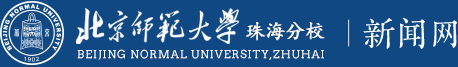人物简介:鄢烈山,著名杂文家、时评家。198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此前做过农民、民办小学教师与中等师范学校函授教师。大学毕业后在政府机关工作。1986 年春进入《武汉晚报》作评论编辑,10 个月后进入《长江日报》评论理论部,曾任副主任;1995 年冬,加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任高级编辑,2012 年退休。已在海内外出版《冷门话题》、《钢丝上的中国》、《点灯的权利》、《中国的心病》等个人文集20 余种,其中《一个人的经典》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另著有传记《威凤悲歌:狂人李贽传》。曾于2004 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 影响(当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 人”。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如何走上杂文写作道路的?
鄢烈山(以下简称“鄢”) :谈到我的杂文写作,我就想起孟子的名言:“予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
少年时代从未想过要当什么杂文家。念小学的时候,曾想像父亲一样当一个农民。念初中时,想长大了当科学家。“ 文革” 开始后回乡种田、当民办教师。一位老教师夸奖我说,小鄢将来可以当中学老师。那些年,最大理想就是转正为公办教师,有朝一日能到公社教初中。1978 年考上大学后,想写小说吧,但练了几次笔,便自认不是写小说的料。我喜欢逻辑思维和大而化之地论事,对家长里短的细节毫无兴趣,永远也搞不清小说家们刻划人物时绘声绘色描写的衣服质料、品牌、颜色。我决定今后从事文学史或语言研究。
不料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了武汉市青山区政府,成了机关里解放以来第一个正宗的大学毕业生。但我的性情颇不适于在党政机关工作。从1984 年起,我开始尝试制作“ 豆腐干”—— 杂谈、杂文、小品文。记得第一篇千字文发表在《湖北日报》上,题目叫《最佳配角》。尔后又写了若干千字文, 得《武汉晚报》杂文编辑刘满元、萧亦聪推荐,于1986 年春进入报界。编言论、写言论,一干就是近30 年。用我们的家乡话讲,是“ 蚂蟥搭了鹭鸶的脚—— 要脱不得脱”。
我就是这样走上杂文创作道路的,岂非孟子所谓“ 予不得已也”? 但从积极意义上讲,这正是由于一种切合自身条件的“ 自我设计”。人,只能在社会给定的环境中生存,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寻求发展;否则,一厢情愿,好高鹜远,怨天尤人,徒然自伤。
记:您的杂文深刻犀利,个性张扬,但与您接触后觉得您很是谦虚低调。为何会出现这两种迥异的风格?
鄢:在生活中,我应该是比较平和的人,这要从阅历和性格两个方面来讲。我的经历还是比较简单的,一直都很顺,从农村出来,当过民办教师、政府公务员然后又投身新闻界。从旁人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社会地位、经济收入都还可以。虽然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但毕竟老家是“ 鱼米之乡”,那种穷得家徒四壁,一家几个人穿一条裤子的情况我从没接触过。相对于许多同辈人,自己的阅历还是比较单纯的,对于整个社会的观察和认识很不全面。为人性格来讲,我不太善于讲话。但并不说明我没有看法。
我的文章是一种思辨性的东西,对事不对人,只要逻辑正确,观点站得住脚,说得尖锐点并无不可。不过我自己也在反省,意识到这样做还是有点问题的。比如前段时间我卷入了所谓的“ 方柳之争”,我对方方说的某些话就不太恰当,太咄咄逼人、盛气凌人,这不太好。
写文章和做人不完全一致,这并不矛盾。写文章批判可以很尖锐,那是思想观念的讨论,但是做人,应该从现实环境出发,一定要平和,对他人多些体谅和包容。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评价和批判是从自己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和自己的良知出发的。文章只是表达自己的看法,但不表示自己就一定正确。因为每个人经历不同,处境不同,观点想法自然也不同,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判定所有人。
做人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孔夫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小时候,我的小伙伴们读书不如我,做算术、写作文不如我,但他们干活比我强多了,他们插秧、挑担、捕鱼捉虾、游泳都比我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你只是比别人知道多一点点,在某一个方面比别人稍微强一点,但比起那些大师来,我们还差得太远了,没什么可以骄傲、高调的。
记:2004 年,您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 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 人”之一,您是如何看待这个“ 公共知识分子” 的?
鄢:“ 公共知识分子”, 首先是知识分子,前面再加“ 公共”,是指关心公共事务,就公共问题发表意见。评断是不是“ 公共知识分子” 还有一个根本标准,就是看是否维护公众利益。大家都在骂孙东东,他说老上访的专业户99% 以上都是精神病。虽然他也在谈论公共问题,但大家不觉得他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认为他是在为某些官僚讲话。所以,这里有一个公众立场的问题,一定要是从公众的利益出发,对社会进言,参与公共事务要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
记:您十分看重“公民”一词,也以“公民写作”自许。那么对于当代大学生,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鄢:“ 公民” 其实是一个中性词,它相对应的是顺民、奴才、暴民,最对应的是“ 臣民”。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大家要做一个公民—— 依法享有当家作主权利的人民的一员。中国的现代化尚在建设中,公民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可以这样自我期许,循名责实去努力,走向公民社会。
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 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现代公民意识,要有社会责任感。这种公民意识不是漂浮于水面勾人眼球的红叶,而似融化于水中的盐分,要深入每个人的骨髓。我最中意的是楼适夷先生的表述:“ 做一个未来中国的公民,为着这国家的建设与成长,而尽我所能尽的力量,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享受。” 目标,是为了中国的进步;尽我所能,是公民的责任;得到应得的享受,是讲公民权利与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楼先生为《东方杂志》1933 年的元旦征梦写的心里话。那时候这是他的梦想,今天我们要将它变为现实。
记:杂文写作有什么技巧和方法吗?能否谈谈您的时评写作方法?
鄢:主要是注意道和术的关系。首先要强调“道”,即你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鲁迅先生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所以你自己要想明白自己要写的是什么,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至于怎么写, 那是术的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
怎么写,要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作技巧,怎么开头、怎么结尾,自己定。你把道理想清楚,做到“ 我手写我心”,怎么想就怎么写,以理服人就行,关键是要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观点。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多读书、多思考,要有独立的人格。
记:谈到读书,现在学生中有一种普遍现象就是碎片化阅读,很少人静下心来品读一些经典。对此您如何看待? 应该如何改变这一现状?
鄢:碎片化阅读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这涉及到博和专的问题。它有好的一面, 能开阔人的知识面, 开阔视野。但是碎片化阅读不专不深, 浅尝辄止。我自己就有这样的教训。我目前的状态其实不是我最初的选择。读北京师范大学我本来是想当老师的,但后来阴差阳错地当上了公务员,后来转行到媒体做编辑,写时评,写杂文,读报纸,阅读就比较零碎。现在又经常忙于刷微博、微信,觉得自己读书太少了。这次来珠海分校的路上,我带了一本章太炎的传记,但只读了两三页。我对古典文化的了解也很初浅。我写的《威凤悲歌: 狂人李贽传》, 其实是我在九十年代初潜心阅读钻研的成果。但现在已经再也找不回那种状态了。所以怎么处理好碎片化阅读的问题,确实非常重要。
要克服碎片化阅读,就要静下心来,好好地读几本书,读经典。读经典对一个人非常重要,我们不仅仅要读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经典文化,还要读西方的经典著作,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的。读经典要先精读,专一门,然后再广泛涉猎。
记:您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当时能上大学的人少之又少。您认为大学教育对您个人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鄢:我们那时候是精英教育,录取率非常低,大家非常珍惜上大学的机会。我上大学时已经26 岁了,我们班上年级最大的同学已经32 岁,都是几个孩子的爹了。同学们读书特别用功,大家天天都泡图书馆,但图书馆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埋头读书。
大学给我很重要的影响就是给了我一个读书的机会,使我有几年能够专心致志地读书。如果我不上大学就很可能继续在中学里当老师,更不会有四年的时间泡在图书馆学习了。当时学校每周六在大操场放一次电影,但很多时候我都不去看,而是到图书馆读书。
此外,大学给了我一个资格,毕竟北师大毕业出去的,平台和机会还是不一样的。
记:很多同学对自己的前途和人生目标感到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对此,您怎么看?有何建议?
鄢:青年人对自己的前途和人生目标感到迷茫,不知何去何从,这是正常现象。同学们还处于青春期,面临着很多选择。迷茫,有一部分原因是现在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政治、经济、技术等方面都在转型,一些制度规范还需进一步完善,社会竞争特别激烈,变化太剧烈,难免让人有些不适应。
面对变化,首先要对自己有信心。同学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好好学习,充实自己,掌握本领,这样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站得住脚。换一个角度想,所谓“ 车到山前必有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要做的就是顺应社会、技术的进步,变压力为动力。
同学们现在的学习条件非常好,网上的公开课一大堆,只要你想学,肯用功, 你可以学习哈佛、耶鲁的课程, 这在我们那个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对于有志气、有能力、肯学习的人而言,将会有广阔的天地,世界将会是他们的。
文、图/廖洪辉
本文原载于《木铎印象》总第02期对话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