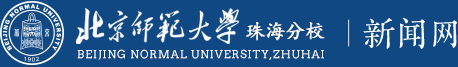“最难忘的比赛永远是下一场。”
“败不是比赛的败,而是内心对于辩论已不再留恋。”
“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我的梦想。”
“当感到疲惫的时候,请尊重别人的付出。”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从来不是辩论本身,而是身边的人的在乎,拼命的在乎。”
辩论场上,他言辞犀利,气势逼人;辩论场下,他温和包容,谦虚有礼。
他是辩论场上的常胜将军,却常说自己是个木讷的人,不善言辞。
他从不怕自己比赛失利,却会担心自己的“孩子”走不出失败的阴霾。
他是校辩论社领队,来自09特许经营学院的曾恺威。
唇枪舌剑,思想的火花在言语的交流中碰撞,站在天平的两端,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这是辩论赛的特点,更是辩论赛的看点。两年前,从第一场辩论赛开始,他便乍露锋芒,从此结下了与辩论的不解之缘。两年后,他已是校辩论社领队,带领着北师辩论队多次迎战外校。沉迷辩论,他有得有失,却甘之如饴,孜孜不倦;带领团队,他有喜有悲,责任压肩,不敢松懈。这便是曾恺威,一个有才更有心的辩论者、领导者。
爱辩论但不会把辩论生活化
大家通常会有这样一个误解:打辩论的人都是吵架专业户,得理不饶人。曾恺威当然也有其锋利的一面,但是他选择了把这份锋利留在赛场上,生活中,他说自己更愿意是一个倾听者,“辩论要求以理智的眼光看待事情,我们不仅要说服别人,还要倾听别人。所以生活中我反而会更乐于倾听别人,适应别人。”同时,辩论也让他学会了换位思考,“碰到不认同的观点,会试着理解对方的苦衷。”
曾恺威笑言,自己加入辩论队的初衷其实与大部分人一样,因为天生不是个外向的人,所以想尝试挑战自我,让自己掌握更多与人交际方面的技巧。然而,当他真的专心于辩论赛后,却因为辩论大大小小的事务忙的不可开交:“3年中与舍友聚餐的次数不超过5次。”
想起之前打比赛的日子,他不禁笑道:“那时是不惜换课来挤出时间准备辩题,就连上课、洗澡都在想着,有时半夜想到一个点会马上从床上蹦下来,有一次因为太过疲倦,竟然在吃饭的时候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如今,这些当初吸引他留在辩论队的原因也悄悄发生了变化,身为队长的他身上有了更多的责任,“从只为让自己获得成长改变为让队伍获得成长。”
爱辩论更爱他的团队
不同于其他文艺比赛的雅俗共赏,辩论赛更像是阳春白雪,只有懂它的人才会真正地热爱。在辩论队里,高年级的学长姐都会把低年级的学弟妹们亲切地统称为“小孩”,曾恺威说,自己打了3年的比赛,基本上没输过,所以对“败”不存过多的想法,但自从当上了领队,带了“小孩”之后开始对成败有了新的感受,“之前我不会因为自己输了一场比赛而伤心,但是当他们输了比赛,我会因为我的队员,我的‘孩子’伤心而伤心。”
大二,他从队员变成了领队,从学生到老师这骤然的角色转换让他感觉无所适从,这时的他遭遇到在辩论队里的低谷期。
谈到这里,他说起了对他影响颇深的一位前辈:宋奎胤学长。“那时宋哥在拱北上班,他特意放下工作和我谈了很多,当时天很冷,我们就在校名石坐了一晚上,第二天清早他又赶回去上班。”这时他停了一下,说道,“这3年来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多厉害的队伍,也不是辩论本身,而是周围人的‘在乎’,拼命的在乎!”
谈到最难忘的一场比赛,曾恺威不假思索地给出了答案:“下一场。”他说:“每一场辩论赛都会有不足的地方,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一直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寄望下一场比赛可以准备的更充分,可以成为我最难忘的比赛。”
爱辩论所以懂辩论
对辩论,曾恺威有属于自己的见解。“感受人人有之,但并非人人会从中悟出道理。辩论的本质其实就是把平常对生活的感受转化为感悟。”他提出了自己更高的愿望:当社会不承认真善美,或忘记了判断标准的时候,我希望辩手可以站出来,传播世人一种更为正确的价值观。
专访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他的梦想,他呆了一下,似乎不知如何回答。“我觉得我是一个实干家,说白一点就是木一点,对生活没什么追求,如果真要说梦想,那就是我接下来的目标——在下一场比赛获胜。”活在当下的人生态度让曾恺威多了一份豁达,少了一份焦虑。
结束了近一个半小时的采访后,他又赶回去和正在紧张训练的队员们在一起,行成于思,辩为心声,这就是曾恺威,他的主题永远不是辩论赛的结果,辩论之外,是他的队友们,是对辩论产生的人生感悟。
励耘报记者:江楚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