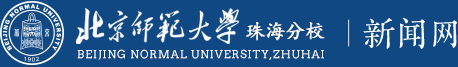华生校长介绍之四
华生的股市变革"三步曲"
赵彤刚
“中国证券市场需要三大制度改革,一是股权分置改革,二是整体上市改革,三是同一股东造成垄断与关联交易改革。”
“这三大制度变革要有秩序地逻辑推进,逐次解决。”燕京华侨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华生用其惯有的慢条斯理的语气,清晰地勾勒出了自己心中中国股市变革的“路线图”。
股改积极鼓吹者
股改如今已顺利实施两周年,在这其中一个慢条斯理的冷静的声音时常回荡其中,让人印象深刻,那是华生的声音。其实,早在1998年2月,华生便发表文章,首次提出A股含权和股权分置改革问题,认为中国股市在表面繁荣背后存在日益增大的制度风险,需要尽早纠正制度缺陷,重新界定产权,用赎买流通权的办法让非流通股恢复流通。
此后,他陆续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和讲话,阐述股权分置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005年初,中央决策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后,在股改的各个主要阶段,华生多次在《中国证券报》发表长篇论文,成为推动股权分置改革权威的理论声音。
2005年2月2日,在中国股市“黎明前的黑夜”,华生发表了《中国股市面临大变革》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是启动股市改革攻坚战的时候了,股权分置改革不能再拖了。”“要紧紧抓住股权分裂这个最大的国情,分清主次顺序和轻重缓急,在解决方案和思路问题上,集中智慧,取得突破。”
2005年5月10日,股指逼近1000点,当市场以猜疑和暴跌迎接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时,华生发表了《市场转折的信号》一文,坚定支持股改试点方案。他指出:“正是在这种熊市漫漫的气氛中,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性转折已经悄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他还在文章中建议投资者把握市场发展的大趋势,不要在熊市的尽头、牛市信号初现时悲观绝望。
而在2006年5月10日股改一周年之际,华生又发表《迎接证券市场的新时代》一文,预告了股市新时代的到来。他在文中预言,股权分置改革将会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时间最短、进展得最顺利,以及对改革成效争论与分歧最小的重大制度变革而载入史册;他同时表示,非流通股恢复流通权过去被视为洪水猛兽,其实,非流通恢复流通股权的实际冲击,会比人们心理预期要小很多。
他的这些话后来和现在都一一被证明是正确和有远见的。
整体上市首倡者
还是在《迎接证券市场的新时代》这篇文章中,华生又一次走在了前面。他指出,在新老划断和全流通新股发行问题提上日程之后,堵塞中国股市长期存在的另一个主要制度漏洞就是非整体上市。股权分置改革解决的是上市公司两类股东的利益冲突问题,而整体上市解决的是控股大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两者都是中国证券市场的重大制度变革和完善。
文章表示,整体上市简化企业治理结构和增加透明度,逼迫企业明确产权结构,用自然人取代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公司控股,让最终控制人浮出水面。对于国企国资来说,整体上市会让国资管理体系直接走上前台,接受市场监督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文章发表后不到半年时间,沪深股市整体上市便风起云涌,市场更是狂热追捧整体上市概念股。
“一年前提出整体上市的时候,市场上还基本没有整体上市之说。当时提出整体上市,主要是从纠正证券市场制度缺陷,在股改之后进一步推进股市制度变革角度出发的。”回想此事,华生向记者坦言。
他说,非整体上市导致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利益不一致,控股股东如果另外还有自己的公司,那么其利益与上市公司利益就会有很大差异。我国上市公司当初多是剥离上市,即剥离一部分优质资产上市,将不良资产留在母公司。但是拥有不良资产的母公司又是上市公司股东,这样就容易造成关联交易、利益输送及信披不对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因此,从世界各国看,整体上市显然是发展方向,而国资委对此也非常支持。股改完成后,非流通股都可以流通,整体上市可以带来国有资产的增值。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国资委的推动与支持,整体上市在各地发展迅速,也成为市场一大热点。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监管部门没有把整体上市作为制度性变革工作来统一部署,没有提出规范性的要求。因此,现在出现了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各行其是,把整体上市作为炒作概念,甚至是操纵股价、兑现利益的途径。”华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整体上市本身没有时间表,市场炒作一阵后,公司澄清没有这个计划,但是没过几天又突然宣布有此计划。时间的不确定性,给市场炒作留下空间。二是整体上市不完整、不规范。假如公司原来有40%的资产上市,还有60%没上市。所谓整体上市就是将其余的60%一起上市,但现在情况却并非如此。
“因为没有规范和要求,所以上市公司可以把60%分成若干份,比如五份,每次上12%,并称是在整体上市过程中。这样就造成了严重的市场信息不对称,把整体上市变成了炒作的题材。”华生不无担忧地表示,并以“播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来形容。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像股改那样,由证监会制订规划与方案,统一部署。”华生指出,“整体上市需要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做保障,因为非整体上市是制度上的缺陷,管理层有责任对其进行改革。”
破解同一股东之惑
“非整体上市这个问题解决后,证券市场的另一个问题,即同一股东关联交易与垄断问题的紧迫性就显现出来了。”华生道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三场变革。他说,同一股东引起的垄断与关联交易,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本质性问题。垄断造成市场经济失效,这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前国资委可能是间接控制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以后可能是直接控制公司。国资委成为上市公司大股东,或是最终股东、实际控制人。目前由于证券市场是国企上市公司占绝大多数,监管机构对国企网开一面,一些原本是关联交易的也被“打擦边球”了。
但是,对于民营企业的上市公司在遇到问题时,其背后的股东及深藏在后面的实际控制人都将会暴露出来。因此,目前实际上实行的是双重标准。比如一些地方国企的大股东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扶持上市公司,给其注入部分资金或实行税收优惠;但这并不算是关联方交易,可以计入公司当年盈利。但是如果是民企上市公司,大股东给公司一笔钱,则可能被认为是操纵利润,这也是双重标准。
华生指出,关联交易虽然从法律上是允许的,但是都有严格的监督与信披要求,包括对权利的限制。因为我国国企上市公司太多,如果都按照关联交易来处理,那么将无法进行正常交易。如关联交易时投票表决,关联方要回避,但是国企上市公司大都是关联的,那么其投票权几乎没有了。而且这样披露也会特别多,每一笔小生意都需要披露;同时,《证券法》规定,要请独立的第三方审查关联交易是否公正,有没有利益输送,会否损害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最后表决时关联方要回避表决,由非关联方投票表决。所以,国内才对国企网开一面。不过,这并未改变法律与经济上双重标准的本质。而且正是由于存在网开一面,所以市场就不规范。“因为规范化的市场,不可能对某一类股东网开一面。”
在非整体上市情况下,国企关联交易利用表面“障眼法”模糊过去了。但是反过来,整体上市却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整体上市后,公司后面的股东将浮出水面,实际控制人也浮出来了。不过,对于同一股东的上市公司,则暴露出两方面问题,一是关联交易,二是垄断。比如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家都是同一个大股东国资委,这就存在垄断。如果监管部门像国外那样保持中立与独立性,那么就应该查这些公司的关联交易了。
华生表示,解决这个问题途径很多,比如股权可以多元化。对于国家不放弃控股权的公司,也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委托给投资基金,就像社保基金那样。社保基金如果以自己的名义一家一家投资上市公司股票,就可能成为很多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是大股东,那么就存在关联问题。但社保基金通过招标,委托多家基金公司代理投资,则绕开了关联这个问题。西方一些规模在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的大型基金,也是通过委托投资基金公司的形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由基金公司派董事,而不是国资委直接派董事。基金公司与国资委是经纪关系,委托期间权利在基金公司。”华生指出了这种模式的特点。国资委将股权委托给基金公司后,基金公司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进行操作。社保基金对基金公司有限制,比如规定不能买绩差公司股票等,国资委也可以对委托基金公司设立附加条件。
华生甚至列出具体的细节:基金公司可以买卖委托股份,但所持股份不能低于最低限度;另外,其所持股份卖出去以后,规定其在一定时间内必须买回来。通过此举,可以保证国家对一些行业上市公司的控股地位。假设国资委委托给基金公司30亿股中石油股份,基金公司可以买卖这些股份,但是事先规定其最低持仓不能低于20亿股,以此进行对基金运作进行限制。基金公司可以据此进行运作,如果认为现在股价高了,可以卖出一部分;过一段时间跌下去以后可以再买回来,变成市场化运作,这是未来改革需要突破的问题。
“这对我国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及干部任命制度,是一个根本性的改革,”华生说。由于基金公司有利益在其中,若管得好,则上市公司将会继续委托,甚至还会追加股份,这样基金公司可以提取管理费。因此,基金公司将挖空心思去寻找优秀的企业管理人员派去上市公司,这就是利益激励机制。国外一些退休基金也是委托给管理能力强的基金公司运作,基金公司为了全力留住这笔钱,需要尽职尽责运作好。
“而如果基金公司都运作好了,不仅上市公司控股权没有丢,而且经济也会得到发展。”华生乐观地预言。
(本文转载自中国证券报 2007年05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