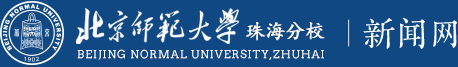2006年5月6日,我利用“五一”长假,和几个学生驱车百里,到南海苏村瞻仰了康有为先生故居。苏村坐落在珠江主干流西流和北江之间一片辽阔的冲积平原上,南望樵山,西接三水,东眺禅城,一条清清的小河从村前缓缓流过,村子周围处处是水,满眼是绿,一看就是人杰地灵、物产丰富的好地方。
康有为故居由康氏祖屋、纪念馆、澹如楼、荷塘、藏书楼、康氏宗祠、大同牌坊、进士旗杆夹等组成。除康氏祖屋、进士旗杆夹为原物外,其余建筑毁于抗战时期,90年代中期康氏堂侄女捐资修复。瞻仰康氏故居之后,我们参观了村内其他家祠、家塾、社学以及邻村亭角村(属三水县)的魁星阁、林氏大宗庙、三圣庙及坊里匾额。这次旅行,增进了对古代岭南农村文化的感性了解。凭借这些感性事物,我们可以更加具体地理解中国古代农村如何治理,“文化底蕴”、“文化积累”、“文化传统”之类抽象的概念也变得鲜活起来。
以康氏故居为主的苏村古代文化遗存十分丰厚。在我看来,它是古代岭南乡村治理结构的生动、具体、有说服力的展示。这种治理结构是以宗族为中心、以教育为基础、以环境为熏陶的一种文化型自治结构。宗族家祠、家塾村学、巷名里称、名人旌表等等,便是这种文化类乡村治理结构的物质表现形态。
首先看宗祠的作用。苏村多宗祠。除康氏宗祠外,站在康氏故居门前,目光所及之处,还有陈氏祖祠、黄氏大宗祠等。我们没有在村中做专门的调查,不过,说苏村姓姓有宗祠,大概是不会错的。在古代乡村生活中,宗祠发挥着多方面的功能。
宗祠是祭祖的场所。祭祀祖先要举行隆重仪式,一年数次。凡行大典,族人齐聚,从而显示家族的存在,强化家族认同与宗族观念。族内讲辈份,长尊幼卑有序,不容丝毫逾越。家族内部的秩序,族长的权威(即乡村中的权威),都来自于以血脉为基础的家族内部天然等级。祭祀祖先是要建立对祖先的尊崇,尊崇祖先,就要遵守祖先的遗教和遗制,祖宗之教不能忘,祖宗之制不能改,祖宗之法不可破,否则就是背宗叛祖,是为大逆不道,这就保证了了传统价值、传统秩序的延续。享受祭祀的祖先不但是始祖或长辈,而且必是祖先中道德文章堪为后世楷模的完人,因此,祭祀祖先,又是回顾家族光辉历史,追忆祖先高风亮节的“历史教育”和“传统教育”。
宗祠是议事的场所。族中大事,如修桥铺路、兴学建校、抚老养孤等等,族长都要召集族人商议,重大事项,往往在祠堂内,当着列祖列宗的面讨论、议决、宣布,以示庄严和庄重。这样,凡在宗祠内决定和宣布的事项,就被赋予了最高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在这里,宗祠又变成了乡村民主的场所。宗祠议事并不必然地代表着族长专制:如果族长有民主精神,他会听取和尊重众人的意见;如果他是专制的人格,也必须遵守而不能抛开这个“乡村民主”的程序。既然是当着祖宗的面议事,族长最后做出的决定必须符合祖宗的遗训,而“祖宗”都是最公正、最无私的,这就保证了宗祠议事的决定一般应符合乡村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可的朴素的公正和正义观念。由此可见,公开性与民主性、公正性有必然的联系。宗祠民主是中国乡村民主的原始形式,原始形式是自然形成的,因而具有最强的生命力。
宗祠是裁决争讼的场所。宗族是乡村生活的基本组织,宗族内部也会发生纠纷,如兄弟反目、夫妻失和、小偷小摸、地界纠纷、伤风败俗等等。古代多数朝代,政权不下乡,即使乡有官员,也无理讼之义务和权利。县官远在县城,离百姓太远,因此,除非命案和其他重大案件,一般纠纷多决于宗族。族内处理纠纷,并非都是简单裁决,一般纠纷须先经长辈调解,特别重大的争讼(极重大者可涉及生命)或调解无效者,最后则决于祠堂之上。祠堂之上,祖宗在前,依家法(主要是习惯法、判例法)裁决,家法制于祖,传于今,威权不下于国法。在祖宗面前有错不认,或不从族长裁决者,轻者“家法伺候”(这里的“家法”,指的是祖宗传下来的象征性的刑具),重者逐出家门,使之成为丧家之犬。在国家政权崩溃瓦解的某些特殊时期,宗祠完全取代政府,裁决所有案件,鞭笞沉潭,火烧自裁,无所不用,目的在维持一方之平安。宗祠裁决族人纷争,甚至取代县官大老爷的时候,表面上是家法取代国法,族长代替县官,其实,宗族内部基本上是一个法治社会,因为族中长辈裁决纷争必依家法,家法名义上制于祖先,实际上是在长期的大家庭生活中自然形成的维持家族内部正常秩序、保持家族和谐和睦的强制性规范。家法制约族人,亦约束族长。族长不依家法而凭个人好恶行事,其裁决就会失去来自祖宗的合法性依据,久而久之,族人便不再认可他的权威和地位,而只有权力没有权威的族长就成了乡中的恶霸,而不再是家族中道德的楷模、公正的象征,在一定条件下,家族便会启动另一套程序来废黜他。
由此可见,宗祠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乡村社会的上层建筑。宗祠以神权为基础,集神权和政权于一体,或集文化和政治于一体,是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乡村政治中枢。这个中枢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它以血缘关系为天然基础,以对祖先、祖训、祖制、祖法即乡村传统的绝对尊重为精神基础,以自然形成的家族秩序、家族和谐为指向,以家族成员参与权和族长决断权的统一为权力结构,在国家权力所不及的乡村,独立地发挥着乡村治理的功能。
我们可以把古代岭南的这种宗祠制度和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作一个也许不甚妥当的比较。两者的第一个区别是乡村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不同。在宗族制度中,族长(有时族长是一个议事团体的代表人物)的权力来源于血缘,授受于祖庙,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与无可置疑的权威,今天的村委会或党支部的权力来自于部分人的授权,这个授权是可变的,没有天然的合法性与权威。宗祠依据家法履行行政与执法的职能,而家法来自于乡村生活的积累与传统,产生和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生活之法、活着的法律;今天的农村仍有乡规民约,实际上发挥作用的是国法,国法是国家权力外加的强制性规范,不少内容与乡村生活无涉,因此国法之权威不如家法。今天的村委会实际上是国家权力的延伸,它的职能首先是代表国家汲取农村资源(如收取税费等等),而宗族的一切活动完全是出于家族的利益,因此宗祠的权威和合法性高于村委会。凡此种种,还可以举出许多。
可以说,岭南的宗祠制度,就是古代中国的村民自治,亦即中国古代农村自然生长出来的乡村民主。退一步说,如果因为在宗族制度下,存在着族权压倒人权的情况,因而不能把它看作乡村自治和乡村民主的一种建构,相对于全能国家治下的乡村来说,以宗族制度为基础的乡村自我组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排除外部力量的干预,独立地管理乡村内部的事务,也还是一种很好的社会基层民主。
苏村的文化遗存,除宗祠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学校。苏村的古代学校,现在看得到的,除了康氏家族的藏书楼以外,还有距康氏故居一箭之遥的“纬卿家塾”和进入康氏故居必须经过的“银塘社学”。康氏是大家族,从纪念馆展出的康氏家谱来看,“有”字辈的已有二十几房,大概族中富裕人家比较多,藏书楼十分宏伟,据说康有为少年在此读书时该楼藏书甚丰。康有为之父,富贫不明,但从其故居来看,不是大富之家,但作为康家子弟,不论贫富,都可以在藏书楼接受家学教育。旁边的“纬卿家塾”,不知当年规模大小,现在只剩一间门脸,显然不属于康家,但也是一所家学,或只为本家子弟所设,或族人共享,不得而知,但清时岭南农村的基础教育由家庭或家族承担,是没有疑义的。家塾之外是村学或社学,村学或社学跨出了宗族的范围,是联办的教育或比较高级的教育。康氏家族的家塾也许有能力承担其子弟教育至他们参加科举考试为止,但较小的或经济力量较弱的家族在完成子女的启蒙教育后,需要和村中其他宗族合办学校,共聘教师,为其子弟进入更高阶段的教育创设条件,为此,就需要结社。村中之“银塘社学”,显然就是当时以结社方式举办的村学。“社”的经济来源是社田(或称“社地”),社田由社员捐助或集资购置,社田之收入用以供养社学。
我们还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家塾、社学等,都建在村庄建筑格局中最突出的位置,均用大块灰白色砂岩砌造,相对于周边民居来说,更加精美、宏伟、整齐,但又朴素无华,坚固沉稳,色彩与绿树、田野、荷塘、水系保持和谐。村学乡校之建筑之所以相对比较高大、宏伟,建造精美,位置显要,自然是要突出教育的精神与文化地位,同时也考虑到对学子们的心理影响,即要通过建筑物的突出位置、庄重造型,激发他们的自豪感、责任心和神圣感。村学乡校之建筑之所以普遍使用大块石料,砖石木瓦等不同建筑材料要融为一体,朴实而不简陋,精美而不华丽,沉稳而不沉重,坚固而不笨拙,宏大而不居高临下,都是灌注了一定的教育理念在于其中,这些深藏于建筑中的教育语言,非对教育有深刻体验与认识者,难以理解。在乡村茅屋中就读的孩子固然可以苦读成才,但他每天走进茅屋书舍时不会油然地感到学校的崇高、神圣和读书人的自豪;几年如一日生活在规划杂乱、色彩灰暗、外型笨拙、华而不实、浮夸怪诞、质量低劣、使用不便、浪费能源、人与生态失和、建筑与环境冲突的校园中,对人的心理健康、品格修养、母校情感的消极影响可想而知!到过苏村以后,我们从此不再赞美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伯克利大学的建筑如何独具匠心,苏村人灌注于村学乡校中的建筑理念和他们一样先进!
苏村的教育遗存说明,古时岭南乡村极为重视教育。人们辛勤劳作,一为糊口,二为后代,办教育就是为后代着想的最好途径与体现。教育责任由宗族和乡村自我承担、自我规划、自我管理。倾一族、一村之力举办学校,虽不乏让族中子弟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的功利性目的,更是为了让后代读书明理,敦仁行义,毕竟不是每个孩子都可以考中举人进士的。
联系宗祠的祭祀功能,我们可以发现,以苏村为代表的岭南文化,其教育层次与教育途径大体为二,一是通过宗祠内的活动,对族人包括青少年进行传统、习俗的熏陶,这是感性的教育,对少年儿童和没有什么文化的人,这种习得式教育最为有效。第二个层次是学校教育,学校教育脱出了祠堂内习得传统与习俗的范围,打开了学童的眼界,让他们走出家族和村庄,进入外部的宏大社会,让他们接受系统的、理论化了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这样,苏村人不但能够习得朴素的、感性的人生信仰与道德规范,而且能够获得理性的、高层次的文化;不但有热爱家族、热爱家乡的真挚感情,而且有了关心社会、献身国家的情怀与抱负。以感性文化为基础,以理性文化为主导,出了祠堂进学校,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层次的科学规划,举家、合族、合村办教育的风气,久而久之,使苏村成为一个文化之村、文明之村,而村民有文化、讲文明,正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基础。仅有以宗祠为代表的乡土文化,乡人没有志向和追求,青年人不思进取,那就免不了会出现坏规逾矩甚至更恶劣的现象,乡村治理可能就不得不借助暴力和强制。有了学校教育,家家有读书人,人人发奋向上,乡村治理的成本因而大大减轻,成效却大大提高。在“学而优则仕”的社会环境中,文化发达与否,甚至成为检验乡村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志。不正是因为苏村出了康有为,我们才这样关注苏村的么?
由此又可以发现以苏村为代表的古代岭南乡村治理结构的另一个特点,即重文化,重教育,重文明,把提高乡村的文化教育水平和文明水平作为乡村治理的基础和检验标准。一个没有文化的乡村,固然可以靠宗祠家庙维持它的秩序,但乡村治理中必然更多地充满了盲从、迷信、朦昧和强制,而不能建立在村民自觉和理性的基础上,而自觉和理性不但有助于提高乡村治理的效率,更能提高乡村治理的层次和效益。
最后要说到苏村浓郁的乡土文化环境。我首先看到、想到的是,苏村的村庄规划、建筑风格等等,无不隐含着深刻的文化与教育意义。我们没有时间详细地观察和研究苏村的整个布局,仅就目光所及,已觉不凡。一进村子,第一个宏伟的建筑物便是“银塘社学”,社学之殿建于人工堆筑之高台上,位置向前凸出,为全村规模最大之建筑。想必因村大于族,故村学位置要靠前,规模要最大。再往里走,便是一个长长、弯弯的荷塘。塘中有水、有荷、有鱼。水者,“上善若水”,流水不腐,无水不灵;荷者,和也,万事和为贵;鱼者,余也。“和”“余”相倚,和谐与富裕,同生共存。康氏故居及藏书楼等居荷塘内端两侧,荷塘靠近村口的外端两侧,面向荷塘,整齐地排列着黄姓、陈姓等宗祠和家塾,其意仍取家家和睦、族族和睦、全村和谐之意。宗祠、社学、家塾居其前,村民住屋居其后,表达敬仰祖先、推崇圣贤之意。民居的规制、风格、建筑材料大体统一,至少从外形上分不出贫富的差别(康氏祖屋也是平凡的岭南建筑,面积不过88平方米)。康有为先生之社会理想乃“大同”社会,《大同书》正是康氏在苏村所著。看来,这“大同社会”的理念和雏型,早已存在于苏村的乡村文明中,因为苏村的村庄布局、文化设施、内部治理结构已隐含甚至体现着“大同”社会的理念。究意是苏村影响了康有为,还是康有为影响了苏村,答案肯定是前者,因为从家塾匾额上的落款可知,苏村的基本建筑早在康有为先生出生前就是这样的格局。环境对人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苏村的里巷名称、居屋题名、楹联匾额、风物景观,无不煞费苦心,使其蕴含教育意义。康氏祖屋在“敦仁里”。《易经》云:“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孔子说:“仁者爱人”。爱自己的家乡,才能爱他人;连家乡都不爱的人,能爱别人吗?所以,修仁,要从爱自己的家乡做起。康氏祖屋旁边有“居安里”。“安”是修身、修养而得的一种境界,安者不燥,不燥则静,静则能思,思必有得;“安”又是“平安”,居家、出外,平安第一。故居旁有芦,名“效贤逸芦”,大概是什么人读书的地方,进了这个房子,就要追思前贤,效法前贤,读圣贤书,行圣贤事。荷塘之上有楼曰“澹如”,楹联释其意曰:“澹看世情多变幻,如能修静得优游”,意欲倡导一种洒脱、乐观的人生态度。康氏故居院中有遗存的进士旗杆夹(旗杆两边的夹石),上刻:“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会试中式第五名贡士 保和殿殿试二甲第四十六名 赐进士出身 朝考二等,钦点工部主事 臣康有为恭承”。宗亲乡人看到那高高的旗杆,除了为本族、本村能为国家贡献康有为这样的人才而自豪以外,哪家不想请皇帝恩准在自家院里也竖起这样一支旗杆呢?
苏村因有康有为而成为南海名村,但古时的苏村大概也只是南海的一个普通村庄而已。苏村临近的亭角村,虽未出过康有为这样的名人,但也处处露出深厚的文化底蕴。该村村前小河(和苏村村前是同一条河)之上有一座三层的宏伟牌楼,朝向村里的一面大书“亭角村”,是为来人指示方向的;朝向村外的一面大书“魁星阁”,而村前与牌楼相对的则是林氏大宗祠。村里的小学生每天出村读书,前有“魁星阁”,后有大宗祠。祖宗的寄托,文魁的前程,鞭策着他们发奋努力,不敢稍有懈怠。岭南乡人如此砥砺子弟,真令人感叹不已!
苏村和苏村式的文化环境仍可视为乡村治理结构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形的精神文明建设。这种精心设计的文化环境,使人无时无处不置身于成乎自然却又独具匠心的文化氛围之中,这样的文化氛围给人以提醒,以熏陶,以浸润,以目标,以激励。家庭的伦理,处世的道德,人生的追求,尽在不语之中。这是一种强大的无形力量,就象你在行进途中背后刮来的大风,推着你不由自主地前进!这是一种特殊的空气,天天要呼吸它,最后就不能离开它,它进入你的身体和血液,就会把你塑造成一个新人。
古代苏村融宗族、教育、环境三位于一体的文化型乡村治理结构,基于血缘相续、永不间断的宗法习俗传承,发于自觉、系统、崇高的理性价值导引,成于亲切、自然、浓郁的文化环境浸润,而服务于建立和维护乡村和谐之最终目的。在这中间,看不到强制,甚至看不到说教,一切都发于自然,亦成于自然。乡村治理主要依靠文化而非物质诱挟或暴力强制,这样的治理层次并不是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可以达到的。
看了苏村,不但更加明白了中国乡村社会能够几千年一贯地保持稳定并成为国家上层建筑之根基的原因,也更加明白了“自古名士出江南,近代风气粤为先”的原因。南方与北方的古代乡村社会,治理结构不同,文化类型迥异,而人才全然是文化的产物,正如旱地出谷、水田产稻,乃自然之理。因此,如何设计和建设大学治理的内在文化机制,营造一个适合于人才成长的文化土壤与文化环境,对我们这些办教育的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